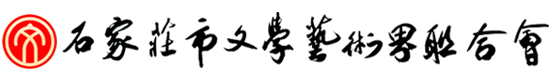三丑爷被人打了。
是谁吃豹子胆啦,竟敢打三丑爷!琴琴和大贵听到消息后,脸都气青了,他们本想立马去探望三丑爷的,但看天色不早了,估摸着三丑爷已经睡下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俩就朝三丑爷家走去。
咱不能忘了三丑爷!琴琴说,如果不是三丑爷,咱还能在镇上摆摊卖菜吗?多亏了三丑爷!
是呵,做人是要讲良心的。大贵说。这也是时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尤其是三丑爷帮了他们家的忙之后,这句话越发频繁地被他提起,动不动就说,做人讲的就是个良心。言外之意就是,如今的人还有几个讲良心呢?
你看看那个马三,当时多牛气呀,可他再牛气也白搭吧,还是不敢得罪三丑爷呗。
哎呀,马三那不是牛气,是坏!坏得头上长疮,从脚底下流脓。琴琴不满意大贵的这个说法,马三光牛气倒不可怕,他牛气他的,于她琴琴又有何相干呢?他万不该支使占奎来砸她的菜摊子,暗地里使坏。马三打过琴琴的主意,却都被她一次次很断然地拒绝了。那一次马三就狠狠地拿眼觑着她说,好哇琴琴,咱就走着瞧——
不久,她家的菜摊子就让占奎给砸了。琴琴出一次摊,就被砸一次。
你说,那天咋就那么巧呢?就让三丑爷碰个正着!琴琴说,占奎刚砸了咱的菜摊子,三丑爷就走到那了。琴琴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天的情景。那天的情景多么让她扬眉吐气呀,完全成了她记忆中最解恨也最快乐的一件事儿。
嗨,真是巧呀,偏偏三丑爷那天就去赶集,偏偏就碰到占奎那小子砸咱菜摊子。
琴琴赶忙接腔,还不是天意呗,我早就说过,像马三那种下三烂,哪能总那么猖狂下去呢?老天爷睁着眼哩,终会有人出来制服他们!虽说琴琴三十多岁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但声音依然又尖又亮,像早春河滩地里刚抽出的苇稚稚儿,不看模样光听声音,准以为她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而且,她身材也没怎么走形,腰是腰侉是侉的,而且唇膏对她来说也是多余的。因为她嘴唇总是那么红,红嘟嘟的像似开非开的玫瑰花儿,往村里女人堆里一站依然那么抢眼。怪不得,马三打她的主意呢。
嗨,到底是人家三丑爷呀,那真是威风!他往那儿一站,冲着占奎吼了几句:人家卖菜呐,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你凭嘛砸人家的菜摊子呢?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还有王法没有?哼,欺人太甚!就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把占奎镇住了。这几年,马三和他那帮小兄弟在这里净干缺德事儿,谁敢这么教训他们呢?镇住了占奎,也就等于镇住了马三!大贵说着眼里放出光来,眼前又出现了三丑爷那张古铜色的脸,以及那两条黑炭般的卧蚕眉。
这不是废话吗?占奎是马三的腿子!琴琴白大贵一眼。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儿,他们的日子过得极平静。大贵呢,每天早早起来,骑上三马车去城里的蔬菜批发市场趸菜,回来,琴琴已把早饭摆上了桌。匆匆地吃过饭,大贵又往城里赶,他在城里一家建筑工地做活儿,是搅拌工,虽说活儿很累人,但收入还不错。琴琴却不怎么着急,她从容地收拾了碗筷,穿戴整齐后,才骑上满载各色青菜的三马车来到镇上,还在那个老地儿,把一个个菜筐搬下来,开始做她的生意。
是马三搅乱了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眼里,那些日子天空是灰的暗的,他们心里也灰朦朦的,像罩着一层总也驱不散的雾气,心里堵得难受。明知道马三在使坏,却又不敢吱声。试想,如果不是因为三丑爷的挺身而出,不是三丑爷那一声地动山摇般的大吼,他们能出那口恶气吗?不可能的。在村里,大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虽说他个子不算矮,模样也说得过去——一张不胖不瘦的方脸,嘴巴和鼻子也算搭配得勾称,但总体看上去平不巴搭的没什么特点,如果把他放置于人群之中,没人去多看他几眼的。当然,模样好赖还是其次,关键是脾性。他性格绵软又不善言辞,一天到晚只知道做活儿,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就等同于一条老黄牛。你说,像他这种人咋能斗得过马三呢?连人家一个犄角也不如!也许,当初马三敢打琴琴的歪主意,并且几次进行试探和骚扰,也是看准了大贵软弱好欺吧。
别看马三在村里奓着胳膊走路,看谁都不顺眼,但他却怕三丑爷。三丑爷自打年轻时就担任村里大队长,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里他带领全村乡亲,将村西那两个伫立了千万年的大沙丘推平,改造成了高产田。那些年,他一直是县里的劳模,更是全村的骄傲和自豪呵。如果把他们村比作当时的山西大寨,那么,三丑爷无疑就是那个扎着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了。后来,年纪大了,三丑爷不再当大队长了,却乐善好施,谁家有了困难他都会帮上一把。总之吧,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因此依然受到全村人的敬重。村里的红白喜事儿更少不得他来主持。三丑爷俨然是伫立在村里的一尊雕像,那是道德的化身呀!
你说,马三再厉害,他敢得罪三丑爷吗?
去看望三丑爷,琴琴和大贵自然不能空手。可买点什么东西好呢?
就为这个,俩人在路上争执起来。
大贵想给三丑爷买两瓶“老白干”,最起码也得五十块钱一瓶的。此外再买上两样儿滋补品,三丑爷上年岁了,需要补一补。
琴琴却不这么认为,她把嘴一撇说,买酒就买酒吧,还买高级补品干嘛呀?二百块也打不住,那得花多少钱?再说啦,用得着买那么好的酒吗?你看你,花钱总这么大手大脚的,钱可是大风刮来的?以她的意思,买上几盘鸡蛋和两样儿营养品,总共花上一百多块钱。三丑爷又不是闹什么大病大灾,只是让人打了俩耳光,买这些东西蛮可以了。
大贵却怪琴琴小气,说,能这样对待咱的大恩人吗!接下来,他向琴琴历数了他们能在镇上摆摊卖菜的种种好处。没错,镇子是个好位置,一条省级公路从中间穿过,两边是挤挤挨挨的店铺,是这一带的经济中心。这几年,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又有开发商在镇上征地盖了楼房,四周围村里的有钱人和一些年轻人,纷纷弃村里的老宅而不住,买楼房住进了小区。镇上人多了,菜自然就好卖,他们的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好。这个地方金贵!
琴琴说,你说了那么多,无非是让我听你的呗。
大贵反问她,我说的就没道理吗?琴琴说,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她是个倔强的女人,平时遇事儿都是她拿主意,这件事儿怎么能依顺大贵呢?
你这话嘛意思?
琴琴把嘴一撇,说,三丑爷帮过咱不假,如今他被人打了,按道理说,咱应该去看望一下。只是没必要买那么多东西,他家缺那个吗?咱表个心意不就得了?唉,真没必要!
咋没必要呢。你,你还有良心没有?
大贵这句话让琴琴非常恼火,嘴唇顿时撅成个红辣椒样儿,狠狠地剜大贵一眼,又恶狠狠地说,你咋说话哩呀?不会说话就把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我咋没良心了?你说呀你?我是要空着手去吗?
大贵被她噎住了,感到自己的确把话说重了。能说琴琴没良心吗?去看望三丑爷她也是极积响应的,而且她一直也在感激他,那是从内心生发的感激呀。只是琴琴在花钱上有些吝啬,平时也是,过年过节去亲戚家,她总是能省一个就省一个,过日子非常节俭。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何尝又不是一种美德呢。
今天他却不赞成琴琴这种做法,就因为是三丑爷,就因为三丑爷是他们的恩人。镇上那么多人,当时都瞪着眼看热闹,咋就没一个出来替她说话,为她打抱不平。哎呀,像三丑爷这种仗义执言的人如今上哪去找呢?做人,可不能这样。
于是,他们又叮叮当当地吵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肯让步。
不去了,不去了!琴琴把手一甩,有几分赌气。
不去就不去!扯淡!大贵将手里的烟用力扔到地上,像以此来发泄对琴琴的不满,把旁边一条狗吓得跳到了一边。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往回走。
这因为这件事儿,他们一直对峙了五天,其实也是冷战,就像两个国家的对峙一样。这期间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也许会引起一场激战,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虽说这期间两人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生计一点也没耽误,依然该吃了吃,该喝了喝,该睡了睡,然而,家里的气氛却不同于往常。这无比压抑的气氛,让人感到窒息呀,时间不长他们就无法忍受了。
他们都觉得自己太傻。是呀,就为一个老头子,他们闹翻值得不值得?三丑爷再好,三丑爷再对他们有恩,不也是个外人呀。为这么一个外人而闹得家里鸡犬不宁,这不是犯傻又是什么呢?而且,他们的对峙和冷战,已经影响到了儿子成成。孩子正读小学,放学回家看到父母亲都冷着个脸,谁也不搭理谁,心里自然不好受,哪还有心思读书呢。
是呀,这是何苦呢?两人都这么想。成成是他们的心肝宝贝,更是他们的未来和希望,明年就要升初中了,哪能就因了一个外人而把孩子的前程耽搁了。你说傻不傻呀?
他们两人都不傻,如今又有几个傻瓜?一个比一个精明!琴琴这么认为,大贵也这么认为。为了儿子成成,他们开始和解了。因为都是一个心思,目标明确,所以两人和解起来非常容易,只需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于是漫漶于两人之间的阴霾就消失了,干净得像大风吹过后的天空。
他们又像从前一样有说有笑了,日子又过得有滋有味起来。
嗨,三丑爷也是多事吧,你说,人家大民在自家地里盖厂房,碍你嘛事呀,你以为你还当着大队长吗?琴琴说。那天,她去镇上卖菜,正好从那儿路过,看到三丑爷站在大民家的家具厂门口,对着路过的人嚷嚷,唉唉,这都是上好的耕地呀,好好的咋就盖上了厂房?可惜不可惜?都像这么下去,甭说三十年,就是再过上十年,人们还有地种吗?地是什么,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呀。没地了往后吃什么?都吃家具呀?吃电视,吃冰箱呀?哼!因为气愤,三丑爷那两条卧蚕眉狠狠地往一边拧着,眼珠子红得要滴出血来。
当时,琴琴看着,听着,在心里就认为三丑爷真是发了昏了,他万不该发这种牢骚,上边三令五申禁止人们占用大田地盖房,能管得住吗?这个村里谁不知道?只要给村主任李大眼一点好处,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因此,这两年村子在以极快的速度扩张,大块大块的田地被一些诸如家具厂养鸡场等吞噬了。
哎呀,这不是跟李大眼过不去吗?三丑爷可捅了马蜂窝哟。琴琴边说边撇了撇嘴。大贵笑笑,附合道,可不,那可是个大马蜂窝!
人家大民当时没出来闹,那是给了三丑爷天大的面子!大贵又说。琴琴笑了笑说,那也不见得吧,大民猴精儿一个人,他知道根本不用他出面,有人会出面收拾三丑爷的,果然是吧。
也不见得,也许是大民找人报复的。
琴琴反驳道,哪呀,大民有那个胆吗?人们都说是大眼干的。没错,大眼干的。
你看这个三丑爷,俩儿子都在城里当公务员,日子过得都不赖,他花吃不清花不清,管那个闲事儿干嘛呀?看看,这下惹麻烦了吧?说难听点,他是吃饱了撑的。
可不呗,真是吃饱了撑的。闲事儿少管,睡觉养眼。大眼是谁呀,他可不是马三,不是占奎,肚里没点套套儿,他能当了村主任?说白了,他是个肚里长牙的主儿,把人带个吃了也不吐一块骨头。这不,有你三丑爷的好果子吃喽。大贵说,他还牙疼般地咂了咂嘴,是替三丑爷惋惜吧。
哟,三丑爷心肠好不假,敢打抱不平也不假,可也得看看对方是谁吧。这几年,大眼他们不就是靠这个肥实了吗?你这是断了人家财路呀,他不急红眼才怪呢。
大贵笑笑说,也真是的,看这个老爷子,不知他脑子里哪根儿弦定错了。嘿,做傻事儿喽!
过了好大会儿,琴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她以胜利者的神态,对大贵说,哎呀,幸亏咱那天没去看三丑爷!
大贵眨了下眼睛,伸手抚摸着后脑勺,说,对呀,幸亏咱没去他家。
试想,如果真去了三丑爷家,让大眼知道了能不给他们穿小鞋吗?三丑爷再有威望,在村里他斗得过大眼吗?
他这是自作自受!琴琴说。
对,自作自受。大贵接腔,唉,看这个三丑爷,大眼平时不能说不尊重他,可他咋就和人家过不去呢?哼,真是老糊涂喽。
可不呗,你还缺嘛呀,就在家安安生生养老呗。村里人都待你不赖,你还管那个闲事儿干嘛呢?听琴琴这口气,仿佛三丑爷就是她的亲老子,她就该这么数落他似的。
之后,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日子就像溪流一般,不急不缓地往前流去,波澜不惊。
如果不是马三的再次出现,他们就会这么平静地生活下去的。忽然就有一粒石子砸进了溪水里。
那天,当太阳收起它最后一束光线,暮色渐渐降临,琴琴开始收菜摊时,忽然,她感觉有一只手搭到了肩膀上,像爬上去一条蛇,一条冷嗖嗖的蛇。
她一惊,忙回头看,又看到那张马脸。在灰暗的暮色里,看不清脸上的神色,而从眼睛里射出的狡狯和幸灾乐祸,她再熟悉不过了。
她一扭身,躲开了马三的手。你,你干嘛呀,大天白日的,再这样我就喊人了。她的声音不大,里面有气愤,但更多的还是责怪,因而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量。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没底气,但明白自己绝不会答应他的。
马三抖抖肩膀,把脑袋一歪,嘿嘿地笑了,她看不清他的牙齿,却嗅到了从他口中喷出的一股难闻的烟味。那烟味令她窒息,她下意识地扭了一下脸。马三说,真会开玩笑呀琴琴,你也不看看这是大天白日吗?你喊呀,喊呀,就是喊下老天来,三丑爷也不会来帮你了。
接下来,马三说了一句很下流的话,但他的口吻却是和蔼的,没有一点平时的那种霸气。然后,拔了嘴里的烟,就扔下一句话“琴琴,你就看着办吧”,转身走了。
不远处就是他家门市。里面已经亮了灯,雪白的光线,洒满门前那块空地,也映亮了门楣上“华威电动车专卖店”那几个大字。
琴琴,你看着办吧。琴琴的耳边,一遍遍地回响着这句话。收拾好菜摊儿,她一边蹬着三马车往回走,一边琢磨着这句话。琴琴,你就着看办吧。琴琴,你就看着办吧。——天上地下,仿佛满世界都是这个声音。所有的声音组合到一起,像高分贝的噪音要将她击碎。
她本来想晚上把这件事儿告诉大贵的,让他想个主意。但她没有开口,不知为什么。
此后的几天,她一直魂不守舍。
马三让她看着办,她应该怎么办呢?她能答应他吗?不,不能,她讨厌马三那张马脸,更痛恨他那双鬼精淫邪的眼睛,她怎么能和这种人保持那种关系呢?然而,如果不答应他,其结果可想而知。而在镇上摆不成菜摊儿,她还能再干什么呢?再说,以马三的霸气,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越想越害怕,每天卖菜时,总感觉身后冷不丁会伸过来一只手,那只手再伸到她的胸前,开始像蛇一样在她身上游走。不,像一只尖利的爪子,因为连接手的那条胳膊上,刺着一只张牙舞爪的老鹰,像随时会把人的眼珠子啄去。要不,就是突然跳出来一个人,也许是占奎,也许是马三的另几个小哥们儿,砸她的菜摊儿。然而,好几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风平浪静。
然而,越是这样,琴琴心里越是不安和慌乱。她的耳边一直回响着那个低沉而又含义丰富的声音:琴琴,你就看着办吧。她觉得自己身边游荡着一个幽灵,这个幽灵和那个声音总是相随相伴,就像闪电和雷声相伴一样。
有那么几天,她怀疑马三就在她身后一遍遍地重复那句话。她扭头看,却没有。她也不敢往他家门市那里瞧,总觉在玻璃门后面,有一双眼睛,一双淫邪的眼睛,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就像一只凶猛而贪婪的豹子,随时会伺机把她一口吞噬。
大贵察觉到了琴琴的异常,问她时,她才对他说了。
大贵听了很是惊诧,但他也没什么办法。对马三这样的人,他能有什么办法呢?甚至,看上去他比琴琴还要紧张。他知道马三的厉害。望着大贵突然变黄的脸和惊惧的目光,琴琴这才明白她当初为什么不肯对他说了。
如果三丑爷还是原来的三丑爷,马三也不敢再打她的主意,他们也不会遭这份罪的。问题是,三丑爷被人打了。三丑爷得罪了村主任李大眼,于是三丑爷不是原来的三丑爷了。
哎呀,还是人家三丑爷,真是咱村一个人物头!琴琴边对大贵说,边摇头叹息。
是呀,咱村里不能没有三丑爷!三丑爷倒了,再没人给咱们撑腰了,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对呀,该怎么办呢,咱们!琴琴哭丧着脸,那红嘟嘟的嘴咧成了苦瓜样儿。
这天晚上,他们几乎没有合眼,一直唉声叹气。两人仿佛走路踩空了,掉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
这时,他们才明白,人一旦失去依靠有多么可怕。在他们眼里,天塌了下来。
不知是谁先提出来,应该去看看三丑爷。
也许是他俩同时说出来的,非常有可能,因为他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他们甚至还想,当初为什么就不去看看三丑爷呢?
是晚上去的,借着夜色掩护,没人注意他们。既看望了三丑爷,又不会让人看到,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好的方式。这一次,他们没有因为买东西而发生争执,完全按照大贵当初的建议办的:两瓶52度老白干,两盒滋补品,总共花去了他们四百多元。
不多,不多!琴琴说。
真不多,三丑爷是谁,咱的大恩人呀。不多!
两人几乎同时说。
秋后的夜晚有凉风徐徐吹着,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条狗顺着墙边匆匆地跑过。其实,天气暖和时,晚上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如今乡下人和从前不一样了,晚上不是窝在家里看电视,就是凑一起打麻将。
是个有月亮的晚上。明晃晃的大月亮挂在天上,往地上铺一层银辉,像落一层霜,洁净,闪亮,能看清散落在地上的小石子和柴草棍儿。
今天是九月十五吧?大贵问琴琴。
琴琴抬头望一眼月亮,月光洒了她一脸。她就盯着月亮说,看月亮那么圆,应该是十五了。几天前,刚过了
马上就到三丑爷家了。他俩恨不得立马见到三丑爷,但又害怕见到,心里矛盾得像自己和自己打架。
见到三丑爷该怎么说呢?都这么多天了!就说,这些天生意太忙,忙得腾不出手来,一直没顾上看望您老人家?但,他们马上又意识到这个理由多么牵强,他们再忙莫非连一点时间也抽不出吗?他们心里发虚呀,不知该如何面对三丑爷。可是如果不这样说,又该怎样说呢?
这几十米的路程,对他们来说,仿佛走了好几年。
终于,他们来到了三丑爷家街门口。
他们同时都呆住了。
那两扇漆黑的大铁门,紧紧关闭着,门前却堆满了各种礼品,有盒装点心,笨鸡蛋,还有营养快线和杏仁露之类;还有水果,像香蕉呀,苹果呀,葡萄呀,等等。月光下,它们五颜六色,尤为好看,闪着一层光亮,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这些礼品,几乎把大门堵住了。而三丑爷家的门楼,显得更为高大,像一座沐浴在月光下巍峨的大山,又像一座伟岸庄重的城堡,通体闪着圣洁的光亮呵。
他们没有伸手敲门。他们不想打破这里的宁静,这是多么壮美的一幅画面呀,他们要让这个难得的画面永驻心中。
他们手里的礼品,自然成了这里的一部分。
他们扭转身往回走,月亮把他们的身影投到了地上。那淡淡的影子,紧随他们朝前移动,像在水底游动的大鱼。
想不到呀,想不到有那么多人来看三丑爷!琴琴的声音又惊诧又欣喜。和来时不同,她两只脚踏在村街上竟是那么有力,两条腿也显得格外骄健了。她竟然觉得自己像电视里袅袅婷婷、风姿绰约的模特。
是呀,真想不到。大贵说,心里也非常愉快,甚至比见到三丑爷还要高兴。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烟,放嘴里一支,吧嗒点着了,深深地吸一口,连烟的光亮也是兴奋的。
此后,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日子又像溪水一样向前流去,波澜不惊。真是波澜不惊呵,因为那个总是在琴琴耳畔出现的声音,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夫了,再也没响起过。她也敢往马三家门市那里瞧了,心里呢,像是有了一种力量,让她不再惧怕马三。奇怪的是,马三再没有来找过她,也没人来砸她的菜摊儿,一切静如止水。
是的,一切静如止水呵。
哎呀,那天晚上真好,看那堆东西,至少有三十个人来看过三丑爷。大贵啧啧惊叹,还伸出三个手指对着琴琴晃了晃。
你说,三丑爷家那个门楼,那晚咋就那么高那么大呢?早先我咋就没注意过?琴琴努着嘴说,她的声音依然那么细,动听得像夜莺的啼鸣。
那个门楼真好看!
对,真好看,月亮也好看,那晚咋就那么亮哩,比白天还好看。
咦,那天晚上看什么都好看,房屋,树木,就像统统用水洗了一遍。
还有你!大贵说,轻轻地笑了一个,有几分诡秘。
你呢,也不例外。琴琴咯咯地笑起来,那细细的声音像月光在村街上流淌。
嗨,看那个门楼,多么有气势!
像一堵墙。
不,像一座大山。
对,像一座山,永远不倒的大山!
大贵说着,感觉自己也高大起来,气壮起来,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原载《山东文学》201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