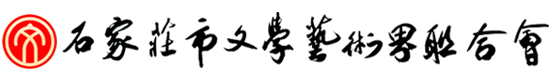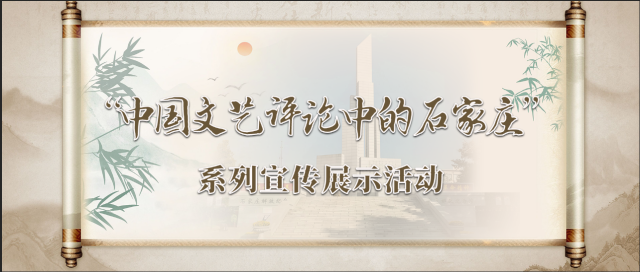
编者按:为庆祝石家庄市文联成立75周年,回顾我市文艺发展的光辉历程,赓续城市历史文化血脉,展示石家庄文艺评论的光荣传统和丰硕成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即日起推出“中国文艺评论中的石家庄”系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既有老一辈作家艺术家身处历史坐标系中的思辨回响,也有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站在时代潮头对现场与实践的理论思考。现陆续选登,以飨读者。
本期推出文章《文学的“求真意志”》,作者陈超(1958-2014),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生前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石家庄市文联第七、八届副主席,第九届委员会顾问。主要作品有《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以及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文学的“求真意志”
“我要听。我必须听——如其所是。”
这是俄狄浦斯对可能知晓其残酷命运的老牧人说的话。他预感到了可怕的生存真相,知道自己已是濒临话语的悬岩。但人的求真意志在此迸涌,使他临渊不惧,并在最后履行了自己的信义承诺:刺瞎双目,让使命和宿命同时展开。自毁双目有如一个噬心的隐喻,它穿透了重重遮蔽的表象,一道尖厉的光芒已深入内心。
每当我读到他这句话,就会产生深深的心理痛楚和眩晕。不要以为俄狄浦斯洞晓的只是他个人或城邦的命运,在我看来,他的遭际实际上预示了求真意志这一人类精神大势的无限期的酷厉发展。尽管我们会为这种永劫回归所主宰,尽管形形色色的斯芬克斯在坠身悬崖后又往往以新的形象面对困境中的人类,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可以和能够放弃作为一个醒悟了的个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坚持探询生存和生命的真相,始于问题,继续更高的追问。这也是我理解的所有严肃文学的前提。

陈超
文学无疑建立在其本体依据内部的一整套复杂关系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封闭的自足装置,亦非高雅人士的话语嬉戏或叙事遣兴。小说和诗歌是对生存境况和生命体验的揭示与命名,一切货真价实的文学,都产生于作家面对生存/生命的遮蔽时,所激发起的深刻的盘诘之情。在作家的巅峰体验中,并不只存在纯审美的迷醉,同时更缭绕着一个固执、沉郁而催促的诫命:“我要听。我必须听——如其所是。”不过,这里的倾听,并不会经由某个深谙生存之谜的“老牧人”告知(对老牧人的期待,实际上透射出人类对绝对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一元论的依恋)。严肃作家的命运甚至更残酷些。他们所企图抵达的生存和生命真相,常常是含混未明的。因此,文学的追问永远不指望有终结的具体的、了然的“地址”,求真意志正是在这种不计代价的语言历险中,发出它奋勇不息的辉光。我要说的是,一代代真诚的诗人作家,如果说他们中真的有“成功者”的话,那也决非指世俗意义上的荣耀,而是他们对生存和生命保持了更尖锐的开掘和追问。他们没有“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加深、扩大、焦迫化;而非是使问题钝化乃至虚假地消失。正是在此意义上,弗兰茨·卡夫卡才说:真正的道路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纠葛地贴着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在众人视为通衢的地方,作家看到了“绳索”;在众人自诩世事洞明的时候,作家提示人们“事情不是你看得那么简单”。真正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和诗——就伴随着这种求真意志和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都是书写族类中的“黑人”,他们不惮于忍受悲慨的遭际,他们知道任何有效的写作,都会带来庞大的生存及权力禁忌对敢于探究其底里者的惩戒;与恒久的集体谎言较力,注定是不祥的。然而,优秀文学的光照,恰好就是不祥命运的赐礼。当我们返观人类的精神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些夙夜匪懈的心灵守护者,他们心力交瘁又生气勃勃。我想,他们首先是古今中外的那些严肃的文学家,而不是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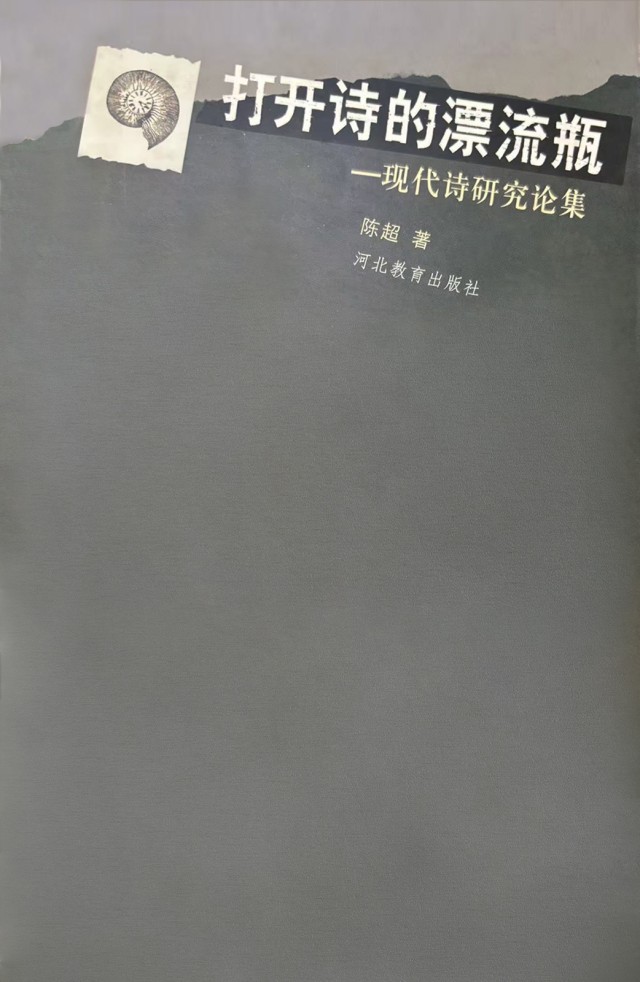
《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书影
当我将文学的维度定义为“求真意志”的时候,我很担心人们将此词语误读。在我个人的词汇表中,“求真”,只是一种“意志”。所谓的真实,在真正的文学家眼里,决非是既在、了然、自明的,它不可能依凭表面的还原主义书写与我们照面;也同样是在这里,文学话语与哲学、社会学话语区分开来了。为了陈述的方便,我且将文学话语之外的其他表述话语统称为“人文科学话语”(实用指称性的日常交流话语不在论列之内)。在我看来,人文科学话语是逻辑的、整体的、类聚化的,它的合法性是通过删除歧见,并否认个体经验的差异和无意识的生命冲涌所取得的。质言之,它祈求的是“头脑”而非“心灵”。这样的话语,僭妄地企图为人类提供某种绝对性和必然性,企图命名在时间和具体生存语境的流动中那个不变的“基础”“本质”。在此,个体生命的痛苦、烦忧、欣悦,以及对世界的奇思异想,都被冷酷而“宏大统一”的整体叙述所抹杀。但是,即使在人文科学和科技话语最为蛮横之际,人类内心深处也总有一种声音在脱离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而片面追求整体顺役所造成的灵魂失落中,倔强地为“心灵”的自由呐喊。这种呐喊的音量不够高亢,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文学甚至是低沉的,但我们知道真正的强音正是低音。虽然严肃的诗人和作家其材料畛域、措辞格局、命名形式不尽相同,但就其精神大势而言,又具有“求真意志”的家族相似性。如果说在米兰·昆德拉笔下,“塞万提斯的遗产”是现代纪元的标识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才真正有效地提供了生命体验中的怀疑精神、多元精神,拯救了卑微的个体生命的尊严,让差异、弱势、局部、偶然发声,它培养了人们对不可公度的事物的容忍力。因此,小说和诗歌中的求真意志是永无终结的。何时“求真”不再作为“意志”,而成为作家自诩的对真实的“定论”,那么这个作家就可能成为被动认同先验“真理”的屈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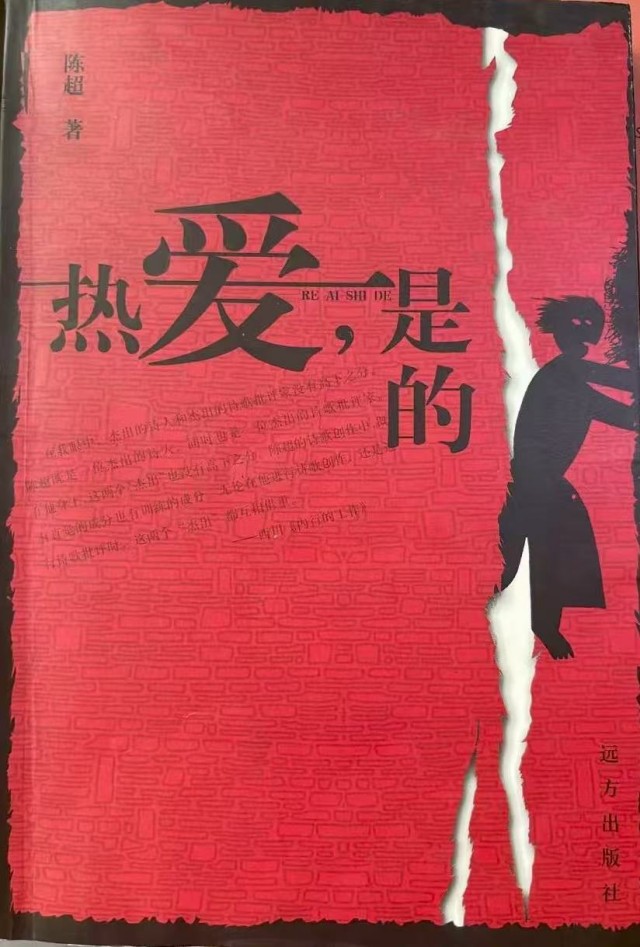
诗集《热爱,是的》
我依然相信,文学是“至深者呼唤至深者”的话语,是人类中部分个体内心巨大焦虑和怀疑的呈现。然而,这里的“至深”,是指生命的体验之深刻,而非单纯的“思辩”之深刻。在哲学思辩领域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黑格尔尝言:“绝对精神的骏马在奔驰的过程中,是不吝惜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的。”对此,我不以为然。我的疑问和信心正是在这里同步展开:文学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对那个唤做“终极真理”“绝对基础”“铁的历史必然性”的庞然大物的不屈从。如果世上没有了伟大的文学家,即“珍爱怀疑的个人”(希姆博尔斯卡语),那么人们很可能一次次周期性地强迫重临集体乌托邦或历史决定论的陷阱。严肃的文学家,不接受任何权力话语的制导,不相信世上有一个绝对的“第一原理”来为人的生命体验规定其永恒的图式。他永远在追问、揭示着生存和生命中的困境,他扩大了我们未知的境域,使人的精神地平线不断后移,使自以为是的独断论者遭逢挑战。一切严肃文学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捍卫人性的迷宫之魅力或曰魔力。我想将这称为现代世界中弥足珍贵的“特殊知识”。在一个“知识”称王称霸的世界上,我甘冒误读的风险,提出文学是“特殊知识”,意在从内部“攻破堡垒”。我用“特殊”来限制和修正知识,是要陈明文学中的求真意志提供给人类的“知识”,是一种与生命深层(乃至诡异)体验,矛盾修辞,多音争辨,互否,悖论,反讽,历史的个人化等有关的“灵魂知识”“经验知识”。在一个思想与科技,意识形态顺役和物质放纵主义同步的集约化、标准化的干涸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提供的“特殊知识”,就不期然中构成了对绝对主义知识、二元对立知识及唯理主义崇拜的颠覆。后者简化乃至抹杀了世界和个体人生的问题,前者捍卫了世界和人生以探询问题的形式存在。在此,“特殊知识”以其特有的细节含义,重新厘定了何为“真知”的维度。文学中出现的“新感性”,就天然地成为否定精神、批判精神、自由探询、生命想像力的接引者。正是在这种变血为墨迹的阵痛中,生存/生命得到强有力的去蔽,语言的深渊被举起,人类被权力话语的高强度刺激所剥夺的心灵活力重新奔涌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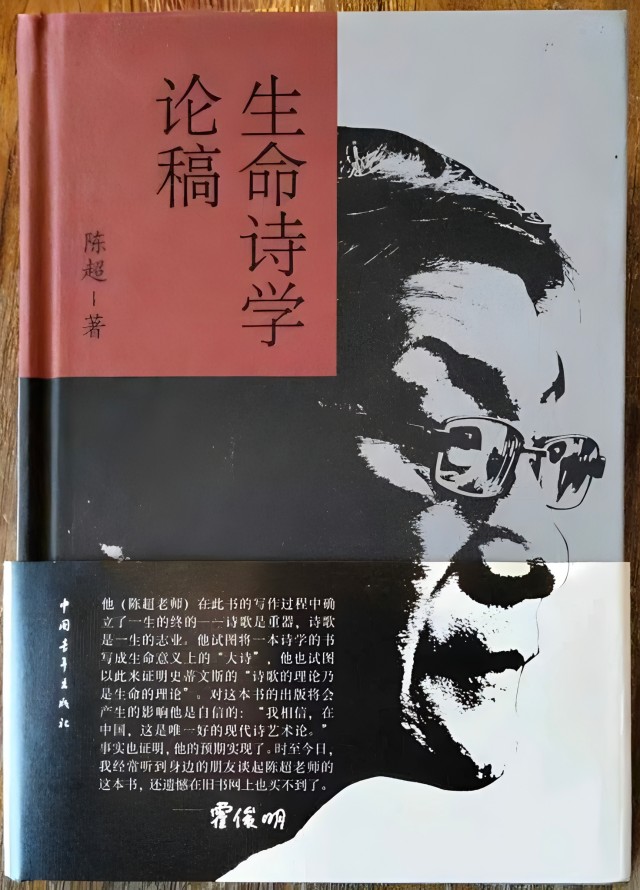
著作《生命诗学论稿》
求真意志或追问生存/生命的姿势,是文学最动人的姿势。然而,我看到目下评论界恰好是在这一点上聚讼纷纭。我认为,许多评论家在指斥先锋文学时,对其“求真意志”存在着盲视。他们有一条现成的鞭子——“历史感”——快意而省事地挥舞在劬劳功烈的先锋诗人作家头上。他们说,先锋文学最大的缺失是“没有历史感”。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优秀的先锋作家声言自己的作品是反对历史感的,那么,问题的核心就不是“小说与诗是否应有历史感”,而应是“如何看待文学中的历史感”了。除去我在前面对文学中求真意志的申说外,我愿意就“历史感”与求真意志的关系,补充如下言说:我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教育小说”。教育小说发轫于欧洲,但在中国五四特别是四十年代以降的接受语境中被渐渐扭曲了。与典型的教育小说(如《威廉·迈斯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理念深为不同,中国的“教育小说”有一个降格以求的想像力原型:相信个人若探索真知、发现自我,必须依赖于某种集体主义的神话。也就是说,欧洲的教育小说书写的是个体灵魂的成长,而中国的教育小说书写的却是对个体灵魂的放弃。这种放弃的程度被奇怪地指认为是作品中“历史感”的深度。在此,人的历史感的获具,不再是基于个体生命的艰辛自我获启,而是对一种既定的“历史风云”、意识形态价值系统的卑屈认同。这样的“历史感”难道是我们需要的么?这样的“求真意志”难道不正是对求真意志的讥嘲么?整个当代文学史前半期,“历史真实”是统摄人心的口号。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历史真实是怎样的呢?无非是对历史决定论的急切归附,是作家对自身本已所剩无多的求真意志的再剥夺。如果放弃个体生命对真实的体验,那么文学只能成为对“历史权力虚构”的邀宠书。正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在这些作品中众多的复杂的个人,变为“一个共名的人”,并美其名曰“典型化”。“典”的什么“型”呢?农民的典型模式是“原过/改过”,知识分子的典型模式是“负罪/赎罪”,底层人的典型模式是“赎身/感恩”,先进人物的典型模式是“升华/引领”,敌人的典型模式是“有产者/残暴”,如此等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崛起方才得到有效扼制。因此我说,与其他文类不同,文学中的“历史感”,是在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处境中产生的。在许多时候,恰好是个人与整体历史或时代精神的错位,才更深刻地带来了文学中的历史感。曹雪芹如此,沈从文如此,穆旦如此,北岛如此,王小波也如此。当我们谈论文学中的“历史真实”时,我们要摆脱那种超个人的、大写的匿名权威——时代风云——的胁迫,回到“历史的个人化”,回到个人的心灵体验的源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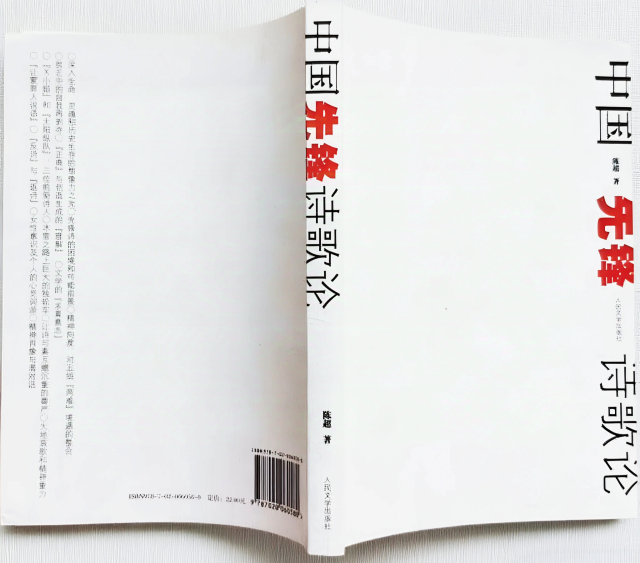
著作《中国先锋诗歌论》
文学中的求真意志就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意志。说到底,生存和生命的问题是永远朝未来打开的,永远不会完成或终结。写出个体生命体验中的历史语境的真实,是所有严肃作家的共同愿望。只不过在如何理解“真实”的含义时,是言人人殊的。在许多作家、批评家看来,文学中的求真意志和历史意识,有赖于“宏大叙事”。他们追索处理的是那些具有社会幅度感、体积感的可类聚的事件。在此,个人的晦涩经验,个人的本真命运就遭到了删除。这种文学作品的声音总是“嘹亮”的,它们曾经体现为体制化的高音喇叭,后来又出现了自封为启蒙“吹号天使”的喇叭,现在则是物欲放纵主义微笑的柔软暴力的喇叭。这三种喇叭虽内质不同,但或有相似的功能:基于一种“元叙述”,一种历史决定论,去遗忘或抹掉个体生命的记忆,简化或嘲弄个人心灵的困苦。与此相反,经由个体生命求真意志濯洗的文学,将历史的沉痛化为内在的个体生命经历,在个体生命存在最幽微最纠结的角落,折射了更为真切的历史症候。他们将个体生命的遭际,总结成特殊的、限量的“历史”,在限量中凸现作家个体主体性的内在深度。在此求真意志中,“越少即越多”,它不是材料体积的宏大,而是体验力的宏大,命名力的博大。同理,当我听到一些论者言及先锋诗人作家“反崇高”时,我想试着反问:难道求真意志本身不正是一种崇高吗?所谓“崇高的消解”,在我看来不过是那种被片面解释的“崇高”的消解。正如阿道斯·赫胥黎在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描述过的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情境:一间宽阔明亮的大厅布满了接通电源的鲜花,一群孩子进入大厅,他们欣喜地扑向鲜花。此时,一双巨手拉下了电闸。这种情形屡次发生后,在孩子心中,“鲜花”与“电击”就具有了奇诡的等式关系。我想,对求真意志贯注的先锋作家而言,所谓“历史真实”这朵鲜花,也由于长期被匿名的巨手通向电闸而变得可怕。他们已渐渐培养出一种警惕的敏识力。他们知道,对“鲜花”的真实领悟,只能经由个人的骨肉沉痛来完成。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此表述为“求真的个人化”,“历史意识的个人化”。它的出现不是“非历史”的,而是有着更为真切的历史吁求。
作为人类“求真意志”体现者的文学,是“混声的独唱”的文学。在这样的文学中,“真实”是一个主权未明的语言领地。文学家不再扮演全知的“圣人”(或代圣人立言者),而是与读者沟通、磋商、周旋、对话的角色。“求真意志”从不夸耀自己,从不封住不同的“我”(个体灵魂内部的分裂和争辩)的嘴,它的价值信念是:心灵的怀疑、追问,远胜于任何既成的理念教条。对“真实”的解释,也永远不会依赖于一个超个人的权威来保障实施。那个“明晰的世界”,“已成的本质”,从未真的存在过;如果小说和诗成为对这些杜撰的神话的流水线作业说明书,那么文学也就成为可有可无的语言游戏了。在这个体制化权力,资讯和声像暴力媾和的时代,文学之所以继续挺身而出,是因为人类需要一种方式来挽留“人的心灵”的声誉。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有关俄狄浦斯的命运的喻象上。在博尔赫斯的《迷宫》中,另一个俄狄浦斯展开了为自己的“音高”设限的追问。“我继续走着单调的墙壁之间可厌的路,这是我的命运。无数岁月,使得笔直的走廊弯曲,成了不知不觉的圆周。灰白的尘土上,我辨认出我疑惧的脸容。我知道阴影里还有一个,他的命运是使长期的孤独厌烦于这座结成了又拆掉的地狱。我们两个在互相寻找。”在这里,诗人揭示了真实的追问者都会遭逢的命运。在求真的孤旅中,没有一个高不可及的外力来帮助俄狄浦斯(“人”)洞彻生存的真相。要解开彼此缠绕的迷宫,只能指望不计代价的个人灵魂历险。所谓“我知道阴影里还有一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另一个“我”。“我们两个在互相寻找”,正是求真意志中“极限悖谬”的最好诠释。
人寻找什么?寻找自己。俄狄浦斯由此变成了内省的新斯芬克斯,在求真意志的激励下,一次次惊愕又犀利地打量着自己。
2002年1月9日至10日
(插图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编辑:封浩
审核:谷雪、李硕
监制:王文静
投稿方式:htypw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