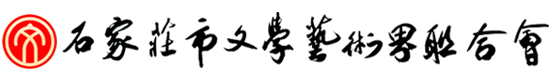在我的印象中,那一个又一个的节日,仿佛是生活恩赐给我们的甜蜜的果实,它包含了浓郁的烟火气,它充盈着丰富的人情味,它让人间的我们更接近了人间。
端午节
如果说春节是孩子们的,中秋节是游子们的,那么,端午节就是上点岁数主妇们的,是她们,在每年五月初五把端午节迎到了人间。
仿佛年轻的人们并不在意这个节日,只有到了一定年纪,才会看见它,才会感受到大自然的讯息,就像只有老人的腿才会感知到明天下雨。
记得我小时候,奶奶会在五月初四包粽子,北方的小院中就飘荡着南国的气息。柿子树新绿而厚实的叶片已足够遮阳,但一阵风吹来,还是会有点点闪光的宝石落在红枣上,落在苇叶上。奶奶会在桌子上放一根筷子,然后将泡在水里的苇叶平展的铺在桌子上,一头就搭在那根筷子上,这样方便打好后拿起来。大概三四片叶子并排并重叠一部分的放在一起,一个粽子的叶就打好了。拿起来向内折,就形成了一个小兜兜,放上糯米和红枣后,将长出的叶片折回去,盖住这个小兜兜的口,最后用线缠紧,一个吊脚三角体粽子就包好了。奶奶的针线活不好,但包粽子的手艺高,直到现在,母亲每次包粽子时都会念叨:你奶奶包的周正,角折的齐。晚饭后,奶奶会让爷爷烧火煮粽子,熟了不吃,要在锅里焖一夜,这样才能让人们在五月单五(我们这里对端午节的叫法)早晨吃上又粘又甜的粽子。
五月单五早晨要早起一些,初夏的早晨刮着清凉的风,在我记忆中留下了夏天最美的印象。这天的早饭便是粽子,粽子上桌后,奶奶会掐我们院中两朵带着露珠的手巾花,插在我和姐姐头上,将一片艾叶放在弟弟头上,并在嘴里念着:闺女戴花,死了不变大料喳(麻雀),小子戴艾,死了不变坷拉块。那时候我虽不懂,为什么要给小孩子送上死后的祝福,但我感受到的是奶奶那充满喜悦的爱。现在想来,这样的祝愿,或许就来源于端午节最长的根须,那是运行了几千年天人合一的理念,当人们将水边的植物作为食物的容器端上餐桌时,心灵就回归了自然,生和死便不再有区别。
我八岁时奶奶去世了,但仿佛母亲还不够老,所以有好多年都是妗子给我们送粽子。
有一回,五月单五早晨六点,风风火火的表哥骑着自行车从三里外的南白滩村,经过一条河,来给我们送刚出锅的粽子。粽子在篮子里被盖得严严实实,没有半点热气冒出来。表哥知道妗子要让我们吃上热乎的,所以他飞似的进胡同时,和迎面一个骑车的老头儿撞了个正着。粽子滚了一地,沾了一身早晨的泥土。这粽子是从老头的篮子滚出来的,原来老头儿是去给他女儿家送的。老头儿一下子就火了:这小子怎么不看道啊!表哥赶紧帮老头儿捡粽子,并一个劲儿的陪不是。老头儿一定想到,进这个胡同,很可能是这个胡同谁家的亲戚,就问表哥去谁家。表哥指着我们家门口,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老头儿立刻温和了下来:啊,走吧走吧。
当表哥描述了老头儿的模样,我的父母立刻就知道是我们胡同南头的大胖儿,是关系挺好的邻居。表哥惭愧地说:人家的粽子都成土鬼了。我们笑开了。虽然经过了一个小状况,但表哥送来的粽子吃到嘴里依然热乎乎的。
后来母亲开始自己包粽子了,仿佛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包了,也就想包了。开始包粽子,也就开始了送粽子。
胡同里八十岁的素彩一个人生活,母亲会给她送几个;大伯母去世后,大伯父也懒得包了,母亲也会让父亲给他几个;三伯母一向不会包,当然也要给他们拿去一些。正因为都知道三伯母不会包,所以他们家的粽子往往是最多的。母亲还会打电话给侄男甥女(我们这里对兄弟姐妹家孩子的统称),问他们包没包,因为端午节正是农忙的时候。
春节和中秋节的礼尚往来,免不了有一些是应酬,而端午节送粽子,却是发心的,是亲友之间纯粹的惦记,是想让你在端午节吃上粽子。
二姨最后一次来电话和母亲闲聊,是四月末的一个晚上。人老了,就不急着睡觉了,而是急着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她们从晚上11点聊到12点,二姨说等表哥买了叶儿和糯米就包粽子,今年早点包。但是,她却没有再吃上粽子。二姨五月初一突发脑溢血,在重症监护室坚持了三天,五月初四凌晨两点,二姨走了。这天我们不让刚从葬礼上回来的母亲包粽子,因为她是那样的悲伤和疲惫,但母亲却坚持要包。母亲安静的包着,一阵阵的落泪。我知道,母亲不能让二姨吃不上粽子。第二天,母亲就把粽子端到了二姨灵前:姐,五月单五呢,吃粽子吧。此后,每年二姨祭日都少不了的一样祭品,便是粽子。亲人之间的惦念,不会因为生死而阻隔。
二伯母说:粽子就得在五月单五吃,过了五月单五再包就不是那个味了。是啊,那个味不只是单纯的糯米、红枣、苇叶的味道,而是端午节的味道。那端午节是什么味道呢?
我想,那味道中,不仅有回归自然的宽广,有龙图腾的期盼,有阴与阳的智慧,有崇尚英雄、崇尚贤德的精神追求,更有母亲般朴素的情怀,那是对亲人的牵挂,那是对晚辈的庇护,是爱的传承。
端午节,它的宽,纵横了几千年,它的厚,蕴藏着中国人的真善美,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我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平常而又经典的端午节。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老百姓对端午节的滋养,才让粽子的味道中有了人情味,多了烟火气。才让端午节充满生命力,就像每年的野草青青。
所以我相信,人间有端午,就有草长莺飞,万物生长。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称鬼节,但这一天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却没有半点阴森感,反而全是热闹和欢乐。
虽已入秋,却还是夏天的阳光、夏天的风,我和姐姐还穿着漂亮的太阳裙,我的辫子绸儿像盛开的浅粉色月季花——粉罗盘,而我们院中还盛开着更多真正的月季花,杏黄田、马克、德国白……像我们这些孩子一样,虽不动声色,却暗藏欢雀。我们在柿子树下,写作业或者下棋。身后的灶台前堆放的很多新柴,灶台的案板上放着早晨父亲买来的猪肉,那时候,村里只有早晨会有一个卖肉的来,谁家要改善伙食,就不能错过早晨的肉摊儿。
七月十五和清明节、寒衣节一样,是给去世的亲人烧纸的日子。奶奶去世后,爷爷去世前,也就是我8岁到12岁那几年,是我们家烧纸的鼎盛时期。因为我们和爷爷住一个院,所以我们这天要迎接五个姑奶奶,两个姑姑,三个伯伯,三个伯母,以及姑奶奶家的孙子孙女、姑姑和伯伯的孩子们。
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一天我家的院落就像90年代的人物集锦,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孩子,以最鲜活的形象刻进了我的心。
这天的第一个重头戏就是迎接他们陆续到场,我和姐姐经常打赌,猜谁先来。
第一个来的永远是三伯,他总会赶在亲戚们到之前来,仿佛这样才算尽到了地主之仪。三伯长得黑,微胖,关键是他总少不了两句抱怨:怎么还不来,让老少闺女们等着他啊。所以他总会让我联想到包公,仿佛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事都有对错之分。
这一天,父亲兄弟四人和各自的媳妇除了重要的事,都会在这里接送、陪伴着老少闺女们,这虽不是上纲的规矩,却是我们家不言自守的家风。
第一个到的亲戚,总会是大姑,大姑进院的第一句话总会说:这天儿真好啊。那时候,有很多人走亲戚或串门,进院后都会以这种方式打招呼,要让屋里的人听到外面来人了。如果有人不声不响地进屋了,会被认为没礼貌。
大姑是个勤劳的人,别看她来的早,其实早在早饭前去地里干了两个小时活了。趁着早晨的凉快下地干活是庄稼人的作息。只要大姑一到场,气氛立刻热起来,笑声不断。大姑说什么都像讲故事一样有意思:这一阵子可是真忙,那过道里连着老了两个人(死了老人),你姐夫怎么得全忙(过去帮忙),那梨树又该打药,五亩都是我和小涛(我表哥)俺俩。夜了黑介九点多才回的家,干脆咱熬个晚,今个出来心静了。
说话间,我的二姑和五个姑奶奶也陆续到了。
除了五姑奶奶穿着现代的碎花翻领小褂,另外四个姑奶奶都是斜襟大褂,而且五个姑奶奶是一样的发型,都是建国初期的妇女们最常见的,齐脖子的青年头,再在耳后一边别一个黑棍卡子。五个姑奶奶的形像,就成为了我心中老婆儿的代表。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们的头发原来和我的父亲一样,是自然卷。看来,这一天相聚的一群人,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有一些是能看见的,有一些是看不见的。
姑奶奶们老模老样,拿的东西也是老模老样的。她们会边说话边从塑料皮编的长方体提篮里,掏出三四包果子(点心)其中的一包,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吃。那果子用桑皮纸包着,用纸绳绑着。一般都是蜜三角、桃酥、马蹄酥,而现在已经绝迹的,是三姑奶奶最常拿的果子,当时我们叫它果子蛋蛋。它类似于现在的开口笑,只是没有裂开,也没有芝麻,而是一个个油炸面球,有红的、绿的、黄的,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颜色,才让我们这些孩子格外喜欢。那时候人们思想简单,串亲戚只拿果子,这也让我曾经以为,果子就是为串亲戚而生的。
当然还会有一些孩子跟着大人到来,记得五姑奶奶的一个外孙女两个孙女特别漂亮,她们比我小一两岁,她们穿着精致的背心短裤,戴着那个年代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警帽,眉间还用胭脂点着一个红点。现在想来,她们的形象多么具有时代典型性,足以登上那个时代的封面了。
人到齐后,同一姓氏的两代儿女便出发了。带着纸钱和祭品,去不远处的另一个家,看望那些故去的亲人。他们跪在几个沉默的土丘前,一边烧纸一边和去世的亲人说话,就像和他们活着的时候聊天一样。我的长辈们脸上没有悲伤,有的只是牵挂和思念。他们关于鬼神的观念都很淡泊,但都特别重视烧纸,我知道这是对亲人的重视,这重视无关生死,亲情不会被生死阻隔。
当父亲他们去了坟上,家里便开始点火熬肉菜了。近三十人吃的大锅菜,母亲说怎么也得客差(小火慢炖)两个小时才好吃。大伯母腌茄子,二伯母切肉,三伯母烧火,母亲作为本家统筹着所有食材、配料,她出出进进忙着。后来每每看到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中四个妯娌一起做饭,我都会想起当时的场景,想必那样的画面只定格在八九十年代的农村了。或许这样做出的大锅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锅菜,因为不仅吃的人多,而且是做的人多。多个主妇一齐下手,多种做法融合到一起,那肉菜就有了复合而丰厚的味道。当然这还不够,还要掺上她们的闲话和玩笑,那味道才算经典。
熬肉菜,是那个时候招待亲戚最好的饭,也是我儿时记忆中位居第一的美味。它的食料只是猪肉、粉条、炸豆腐块和一种时令蔬菜,冬天是大白菜,秋天是冬瓜,春天是圆白菜,而夏天便是我最爱吃的茄子。把茄子放在肉菜里,让茄子有了肉香,那茄子比肉还好吃。那时候,虽然从经济上说,每家都有了随时熬肉菜的能力,但人们的观念仿佛还没有跟上,平时熬顿肉菜还是需要理由的。所以,我对七月十五的期待,是少不了这顿美味的。
影壁前的两棵大槐树下,放上两张方形的、低矮的桌子,桌子上放着烧鸡、火腿、花生米。两张桌子难以围坐这么多人,大家就各自找地方坐。大姑瘦,一块砖头也能坐,她左手的前三个手指端碗,后两个手指拿馒头,右手拿筷子夹菜,吃馒头就把筷子往后一攥,拿起左手的馒头咬一口再放回去。这种吃饭的技能,以前还是很常见的,或许只有集体吃饭才能练出来吧。
大家看似随意,其实有着内在的秩序。小辈们一张桌子为中心,长辈们一张桌子为中心,而且一定要安排姑奶奶们坐好位置,并且先把肉菜端到她们前面,馒头筷子什么的,一定要及时照顾到,母亲一顿饭坐不下。父亲就守着我们,把他碗里的肉都给我们。
那时候,汗珠一个一个从耳边滚落也不觉得热,那时候,知了在槐树上不停地叫也不觉得烦,那时候,肉菜的香气一阵阵的飘,一直飘到了现在。
午后,我们这些孩子会在我的屋里吃冰棍、看电视。姑姑和姑奶奶们会在爷爷屋里坐着,而我的伯父伯母,不管上午来的早晚,下午都要和姑奶奶们正了八经的说说话,如果有时间,最好在姑奶奶走的时候能赶上送她们,那才算完整尽到了礼数。
如果说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那便是礼数。这个礼数,并不意味着腐朽,而是敬重。敬是互相之间的感恩,重是对亲情的看重。礼数就成了含蓄的我们的表达方式。
我一直对相敬如宾这个词感到无法体会,心想亲人之间相敬如宾岂不是太见外了。那次姐姐说可能就像爷爷和姑奶奶们的状态吧。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个词。
爷爷排行老二,五个姐妹当中唯一的男丁,按照过去的价值观,在家庭中应该是众星捧月,但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凡事都为别人着想。爷爷和姑奶奶之间的相处我并不了解多少,只是在家人的话语中听到了一些。三姑奶奶膝下无子,爷爷就将二女儿过继给了她,尽管奶奶为此抹眼泪,但她知道爷爷不可能让妹妹孤独终老。五姑奶奶的婆家近,回娘家多,她只要来了,奶奶就立刻烙饼,天黑了,奶奶还要把五姑奶奶送到婆家村。姑奶奶们的丈夫如果来了,更是会抬为座上宾,爷爷不喝酒,但却会陪着妹夫喝。姑奶奶们对哥嫂也是格外尊重,说话都是恭恭敬敬地,以至于我小时候以为爷爷奶奶是她们的长辈。奶奶最后的那段日子,姑奶奶们频繁探望,尤其是三姑奶奶和五姑奶奶,加入了儿女的行列,在病床前照顾。给奶奶穿寿衣前,三姑奶奶还在自己身上穿了穿,说这样奶奶穿上了舒坦。看到他们之间的情义,小辈们私下里自愧不如姑奶奶想得周到。
亲人之间能做到相敬如宾,不仅是对亲情的看重,对人和事高度的认识,更是普通人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每当落日还剩一些余辉,姑姑和姑奶奶们才不得不离开。母亲说,闺女回娘家,总是待不够。这时我的父母拿出了早已按照爷爷的指导备下的回礼,送至大门外。
时光总是悄悄地改变着一切。记不清是哪一次送她们走,却送走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大家庭的时代,是烧纸的时代。
如果说曾经烧纸的日子算是一个节日,那我更愿意称它为亲情节,血脉相连的人,无论生死,这一天都能团圆。它不像父亲节、母亲节那样单一具体,而是更加广阔。谁的血液中没有兄弟情、姐妹情、姑侄情、爷孙情,它不具有代表性,却同样伟大浓厚,持久的为每一个人提供着赖以生存的温度。
如今,爷爷、四个姑奶奶、两个伯母已去世,我们这一代虽已长大,却都被淹没在各自的忙碌中。在这个电话不离手的年代,却再也聚不齐了。
以前,人就像长在藤蔓上的果实,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身边是谁,知道自己根在哪里,那根须深深的扎在土地里。而现在,人们就像水中的浮萍,尽管身边尽是繁华,但匆匆来去,都是过往,每一个人都带着迷茫漂泊,每一个人持久的陪伴者只有孤独。
重阳节
曾经,九月初九是我们县城一年一度的九九庙。庙会在解放前还是名副其实的庙会,称之为钱粮开柜庙,解放后为了破除迷信,改为了物资交流大会,文革时期取消,文革后又恢复了。我的父辈们也没见过九九庙的诞生,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九九庙就像土地一样,是原本就有的一部分。
庙会为期五天,唯数第一天赶庙的热情度最高,村里虽不是万人空巷,但绝对能看出冷清来。长年不去城里的老头儿、老太太,也会在这一天把自己收拾的利利索索的去赶庙;再忙的庄稼人、家庭妇女,也会在这一天放下手里的活儿去赶庙;住在城里的人,都会邀请村里的亲戚们去赶庙,这一点已成为了约定俗成的礼节;就连村里的小学也会放假两天,孩子们又怎么能不要去赶庙呢。这一天的傍晚,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准是:赶庙去了没?去过的人总会感叹道:人太多,有什么啊。但这并不能减弱没去的人的向往。
这一天没去的人总会有些缺失感,尤其是孩子,不管大人不带他去的理由有多充分,这一整天还是会没好气,我就多次成为过那个没好气的孩子。写作业就是踏不下心,下棋、画画也无趣极了。我的母亲也是心不在焉,她会冷不丁地说一句,看起风了,准刮赶庙的人一身土。听到她这样的安慰,我就更来气了。
坐轮椅的我们,并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一辆自行车就带着去了,我们去,就要全家出动,父亲还要去5公里以外的桥头,雇一辆摩托三轮车,那种出租车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就像小型货柜车,拉人也拉货。那样的车可以把我们连人带轮椅直接抬上去。如果赶上比较小的,还得雇两辆。但我的父母并不嫌出行麻烦,而是担心我们的身体。九月初正是秋冬交替的时候,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风,要不是艳阳高照的极好天气,父母是不敢带着抵抗力低的我们出门的。幸好有那么几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也让我和其他孩子有了更多共同的回忆。
我最早的赶庙记忆,是我七岁的时候。像那时候大部份庄稼人一样,父亲开着拖拉机,拉着我们姐弟三人、母亲、奶奶和一车的兴高采烈,车厢里铺着棉被,母亲和奶奶头上的三角巾随着颠簸而颤抖,而我们总是不停地说话。一路上总会不断地有邻居、亲戚路过,总会不断地打招呼。
在庙会上遇到熟人,绝对是庙会吸引人的地方。你来了,我也来了,这样的赶庙才有意思。
路边拥挤着卖衣服、鞋帽、布料、气球、玩具的,摊主和顾客们都在喊叫着讨价还价;炒饼、烩面、大锅菜、炸油条、烤红薯的香气随着飞扬的尘土,一浪一浪的诱惑着人们;马戏团的大棚前、文艺表演舞台前、变戏法的吆喝声前更是人山人海。我们跟着潮水一般的人群涌动,我把刚买来的面包圈戴在了手腕上,感觉这个能吃的手镯好玩极了,可是我的视野比较低,看到更多的是人们的后腰,我就在晃动的人缝中张望。那时候还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我坐的还是竹子做的婴儿车,人多的地方根本走不动,父母就在我的前面倒退着,拉着我的小车走,边走边喊:借过借过。父母就让我们和奶奶在馅活儿(馅盒)摊稍等,他们去前面看看。
我们看拥挤的人群,无论是穿着中山装满脸皱纹的老人,还是穿着牛仔装的小青年,他们的眼神都特别的干净,仿佛前方有他们各自的幸福。不一会儿功夫,就有好几个熟人路过,奶奶和他们打招呼,我也记不清他们说了什么,只觉得他们都特别高兴,而且格外亲切。其中一个是大姑父,大姑父人实在,见了我们和他的丈母娘,自然要破费了。他给我们买了几个现做的白菜肉馅的馅活儿,那馅活儿又软又香,可是吃着吃着馅里有个土坷垃,我们觉得很可笑,但并不想为卫生问题找摊主。
那时候,我像其他赶庙的孩子一样,心里还藏着一个任务,那就是买到过年穿的衣服。所以到了童装集中的摊位前,我就睁大眼睛找。那次总也找不到喜欢的,我就有些着急了。但是我的父母却非常有耐心,尤其是我的父亲,哄着我一件一件的挑。现在想来,当今的父母们,早就不耐烦了。就在快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被一件大绒袄罩吸引,大红色的布料配上雪白的人造绒大翻领,腰间还有一根抽绳,既华丽又可爱。父母以当时不菲的价格买下了。多少年过去了,这件衣服依然在我的衣柜中,小小的,却毫不退色。
赶庙的孩子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想错过庙会上的任何地方,这样回去和孩子们交流才有资本,最好是别人看到的我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我也看到了,那才神气。在庙会上,我弟弟抽奖抽到了一个洗脸盆,我们看了蟒蛇表演,我们遇见了抓小偷的,回去后我就给别的孩子讲了好多遍。
接近傍晚的时候,街上的人少的许多,声音也少了许多,地上随处可见糖葫芦棍、包装纸、甘蔗皮、桔子皮,偶尔还会有一只踩扁的婴儿鞋。现在想来,其实并不是有了庙会,才有了赶庙的人,而是有了赶庙的人,才有了庙会。那庙会,又何尝不是那个年代男女老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聚集起来的呢。
带着新衣服、好吃的和干裂的嘴唇、一身的尘土,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拖拉机离庙会越远,庙会在我心中就越往上升,直到像那夕阳一样,在我记忆中闪闪发光。
慢慢地,购物方便了,出行方便了,天地阔宽了,幸福的标准提升了,仿佛生活中处处是庙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赶自己的赶庙,所以,九九庙便在经历了两年冷清后,被取消了。从此九九庙就留在了曾经的岁月里,但它散发出的光芒,在我心中却越来越亮。
过年
我小时候,不知具体哪天算过年,就问父母。父亲说,大年初一是春节。母亲说,年三十儿也算过年。父亲又说,正月里都是年。听了他们的解释,我就更糊涂了。长大后,我才慢慢领悟到,过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
那时,每当迈进腊月的门槛,过年,这个词出现的就越来越频繁。“把凳子修修吧,过年来人多还坐呢。”“赶集去该买过年的粉条了。”“过年谁谁就回来了。”“过年呢,不许……”“过年呢,就要……”年味儿就在这不断地提起中越来越浓,直到过完正月,再在恋恋不舍中散去。
随着过年被提起,带着年味儿的物和人陆续来到家里,带着年味儿的事也开始不断发生。无论是平时就有的米面油、肉蛋菜,还是稀罕的金针、木耳、带鱼,无论是生活常用的笤帚、蒸布、碗筷,还是过年特有的:春联、灯笼、吊挂、鞭炮,都被称之为年货,只要被称之为年货,就都带着年味儿。而这段时间来往的朋友,走动的亲戚,也都带着年味儿。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朋友们会在正月里聚会,亲戚们会在年前拜访。尤其是看望长辈,一年当中再忙,过年上门的问候不能省,不然就失了礼,就忘了自己是谁。无论来访者还是主人,都是喜气洋洋的,是过年,让所有人放下了平日的忧烦。
每家都开始忙碌,打扫、拆洗、赶集、制作各种美食。平时也做的事,过年做就不一样了,每一件事,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讲究的。就拿我们这里来说,过年要蒸笼糕、花糕、肉糕,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还要准备糖果和干果,不仅为招待来客,更寓意着来年的日子香甜。过年蒸馒头,面发的越欢预示着来年越兴旺,每每看到面起得满盆了,母亲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高兴:起好了!过年再懒的人家也要大扫除,不然就会留在旧年。虽然大年三十是最不着急出门的一天,但每家都在暗中比拼,看谁家最先包完饺子去放炮,因为这说明谁家是勤劳之家,好运气自然先到谁家。除夕夜煮饺子要烧芝麻秆,寓意来年生活节节高。煮得饺子要留下一些,留到大年初一,寓意着来年不会饿着。年初一不准开柜,要穿的新衣服得除夕晚上拿出来,这样老鼠一年不会来捣乱。这一天也不准扫地,不然就会把福气扫出去。总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重大而美好的意义,虽然还是熟悉的地方,是日常的事,但都非常神圣、正式。
在过年的日子里,无论做什么,都是在进行一场仪式,都是这场仪式的一部分。
除了有实际价值的事被赋予了仪式性,还有一些纯粹的仪式性活动。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正月十二不睡早,听老鼠娶媳妇。正月十六转寨墙,一年不腿疼。那时候人们对这些事是格外用心的,如春联,大部分人家都是找人写,甚至自己编。我们家的春联都是父亲创作,记得我七岁那年春联写的是:换来精面油满瓮,买来彩电购纱灯。虽然没有什么文学水平,但如实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生活变得富裕的心情。
还有一些仪式活动,虽如今已经消失,但却在我记忆中代表着浓郁的年味儿。
除了约定俗成的仪式以外,很多人家还会用独特的方式,体现出过年的的心气儿来,比如我们家。
我十一岁之前祖父还健在,他每年都会自己制作过年的灯笼。一进腊月他就开始不急不慌的预备材料,铁丝、白纸、颜料,开始检查毛笔、钳子这些工具是否好用。他会将铁质的灯笼架拿出来,灯笼架是一大一小,长方体,大的两尺高,小的七八寸高,铁架周正,花式精美。祖父会先给它上油明漆,哪里坏了再修一翻,然后糊上白纸。大的挂在影壁和大门之间,小的挂在大门洞里,当灯笼里面的蜡烛被点亮,整个院子都沉浸在一种喜庆又庄严的气氛中。
最特别的,还是祖父做的靠山灯。两个灯笼的形状像两面鼓,靠在影壁上。这是祖父的重头戏,他不仅要糊纸,还要在上面作画写诗。祖父每年画得画都不一样,要有一些故事情节在里面。所谓的诗,也就是顺口溜式的注解。小孩心思不在这上面,所以我记得画面很少,只记得有过老虎、大胖子、穿蓑衣的老人。这两面靠山灯正对着大门,蜡烛点亮后,总会引来邻居们的欣赏和夸赞。
祖父走后,没有人再自己制作灯笼了,他带走了很多年味儿。
而年味儿最浓的就是磕头了。
大年初一早晨是仪式最多的时候,我的祖父母、父母会四点起床,俗称起五更。他们先给各路神仙摆上供,再准备好上坟的用品。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和我的三个伯伯、我的母亲就和我的三个嬷嬷走出家门磕头了。
磕头,就是每家已婚男性以兄弟为小组,已婚女性以妯娌为小组,去给村里的大辈和兄嫂拜年。主要是一个家族中的,有一些不是一个家族的亲近的乡亲大辈也要磕,大部分人要磕大半个村子。这也是新一年第一场热闹。
清冷而新鲜的风让干净的街道更加干净,让喜庆的灯笼、春联、吊挂更加喜庆,也让热情相互拜年的乡亲们一点不觉得冷。每一个人都穿上了新衣,笑容也是崭新的。这个仪式就像整个村庄的大游行,但大家走的不是一个路线,因为人们都是几代人在一个村繁衍生活,每家都有庞大的家族系统,所以这路线就是宗亲脉络的外化。
我家在村里辈份大,我的祖父母不必出门,只在家里接待来磕头的人。我们小孩儿自然是看热闹的。毕竟是冬天的早晨,大人不让我们出去,我和姐姐就在棉门帘缝处往外看。磕头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来,他们带着喜气高声喊着爷爷奶奶,祖父母就去迎接,来人见到主人了就磕头,同时说着:给您磕这儿了。我的父母外出磕头了,但也不能少了,来人会再磕两个,同时说着:给我叔叔婶婶磕这儿了。祖父母就热情地说:都有了,都有了。意思是一个就代表了。但人们那时候都特别实在,一个都不会省略掉。还有幽默的人就会说:我张着包呢。很形象地表示每一个头都收到了。平时非常熟的人,这个仪式中竟有了些正式感,也正是这正式感,让我觉得这些人格外亲切。我们家大概会陆陆续续来二十多拨人,气氛非常热闹。
人们的亲疏关系、家族位置、长幼身份,在这一仪式活动中,再一次被确认,人们对待他人该有的态度基础,再一次被强化。
但渐渐地,人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忙碌,也就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平时不联系的宗亲越来越陌生,以致于再进行磕头这个仪式时,都是给不认识的人磕了。这就让这个活动显得多余和莫名其妙了。直到有一天,以移风易俗的名义,把这一磕头活动取消了。从此,人们对家的概念,也就只剩下了单一的小家了。
慢慢地,不仅是磕头拜年,很多过年期间的仪式都消失或淡化了。
这几年每到不像春节的春节,总会感到冷清,但冷清中,我仍能闻到年的味道,所以,在过年的日子里,我会带着庄严和喜悦去做每一件事,把过年的日子过成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
(以上作品刊登于《中国作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