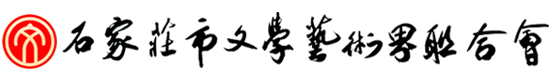艾蔻的诗集《亮光歌舞团》分为“小人间”“臭弹”“青少年须知”“玛花的决心”四辑。书中既有童话幻境单纯斑斓的心灵词源,又有独立女性在丛林世界的精神探险;既有对日常生活和文化困境的反思追问,又有对复杂人生与历史话语的梳理发现。艾蔻在诗歌中建立起一种更富于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同时回馈到她的军旅诗歌主题创作中,以个人化丰富的想象力,对军旅战斗生活进行多维重构、整合塑型,令人信服,又精彩绝伦。
18年前,艾蔻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到石家庄一所军校任教。那时,艾蔻偶尔出现在河北的诗歌活动上,极少发言,却令人瞩目。艾蔻出生于新疆库车,成长于川东南丘陵地区,又到湖南长沙读大学,小小年纪已辗转多地,没有被乡愁地理束缚,百味人生无所禁忌,万里江山皆入画图。
“国王搬进新的城市/蟋蟀变成流水”(《新的争议》)、“看似无关的桃树/正挑灯夜奔”(《有棵桃树的清晨》)、“天生的逃跑家/在挣扎中学会潜伏/或者骑着浪花逍遥远处”(《海盗公开承诺书》)。艾蔻的诗歌,呈现一种梦幻奇诡的童话寓言色彩,像波斯菊一样,有着羞涩中的期望和喜悦中的不安。与雄浑苍莽的太行山相比,波斯菊的火苗虽然微弱,无法撼动河北诗人群体浓厚的恋土怀乡情结和现实主义美学传统,却让冻土融化,滹沱流澌,再起微澜。
“没有精灵的诗是没有神的庙。”九叶派诗人郑敏如是说,“诗的精灵神秘地出没于诗人的地平线上,忽隐忽现,这是创作的开始,是对创作的召唤,对创作的诱惑。”读艾蔻的诗集《亮光歌舞团》,感觉脑海中不断有精灵飞舞,有的精灵藏在意象中,有的精灵躲在句子里,有的精灵潜伏在整首诗内,给人无限的遐想和陌生感。
与“70后”诗人普遍有着乡村生活经验、对城市生活保持着警醒和疏离不同,艾蔻这一批“80后”“90后”诗人,人生经历各异,社会分工更细,繁花似锦的时代,让每个人都活成了他们自己。我们的诗中有大地、麦田、向日葵,终生受泥土束缚;她们的诗中有巫师、骑士、精灵,能够驰骋飞翔。卡尔维诺认为,“童话能够利用最少的工具实现最大的效果,它色彩斑斓、变化莫测、显而易见、至关重要又稍纵即逝……童话犹如一颗充满魔力的核桃、榛子或是杏仁,虚构作品的作者在它内部所能寻获的不是珠宝或金钱,而是整个叙述文学的宇宙和灿烂的星空。”
我认为,诗歌创作也应如此,不断减少工具,让语言恢复本能,让想象力自我启动。我们的诗歌,过于依赖经验的逻辑,而有时经验是不可靠的,久而久之,形成了写作模具“范式”,一种理性掩盖之下的平庸。优秀的诗人,必然像庄子一样,以看似无逻辑和非理性的天马行空,呈现内在独特深刻的思想性,寓言和童话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出口。从李商隐的《锦瑟》到纪伯伦的《沙与沫》,许多优秀诗人的经典作品,都有童话的成分,又因减少了工具,呈现出非理性的跳跃和晦涩难懂的细节,但不管怎么变幻,依旧有草蛇灰线可循。艾蔻的诗歌,亦是如此,含有童话成分,但并不是低幼文学,读起来有些晦涩和跳跃,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让我想起俄国艺术家马克·夏卡尔画笔下万花筒般的世界,绿色的牛马,飞在空中的恋人,以梦幻、象征性的手法与色彩游离于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之外,让人慨叹在萨尔瓦多·达利、巴勃罗·毕加索的沉痛悲愤的黑铁时代,还有如此多彩、轻逸又不失深刻的画家。
艾蔻没有像大多数女诗人那样经历漫长的“自白”倾诉期,但她依然有故乡四川先锋诗人翟永明那种“女性意识”和“黑夜意识”。艾蔻写了《开颅术:脑瘤摘除》《流产之歌》《终极审判:脐带》《青少年安全须知》等小长诗,写出“孩子会远离我/要成为眼泪/就必须离开眼睛/故乡它永远在山上/不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下山的表情”等精绝的诗句,从自然属性到母性,从化学到医学,将医学院校专业技能与广泛的日常经验、历史、文化融合,做寓言化的处理并重新命名,将海沙捏合成珊瑚藻礁,让鱼儿、螃蟹、海螺自由栖息成长,既有女性的自强,又有母性的慈祥。
艾蔻身为军医院校化学教员,元素周期表烂熟于心,诗歌难免有试验的成分,有很多令人错愕与惊奇的地方。诗歌是非理性的,化学分子式往往具有“不对称之美”。化学元素像诗一样,是单纯的,但提纯的过程是复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以说,越活跃的元素越危险,艾蔻的诗歌,饱含放射性元素,在灿烂的表象之下,有着炸裂人性的锋利,譬如“他把自己摁到墙上/空荡荡的墙面/也接受了来自异星球的光/两极相认,越来越软/它是他地下的四年,他是它/仅有的七天/时间开始融化/每件事物即将到来”(《七日蝉》)。
李清照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不只是因她写下那些流传深远的婉约词,而是彰显爱国情怀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以及“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打马赋》)同样,艾蔻没有把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诗歌技艺消耗在个人私域抒情中,身为军旅作家,她一直以歌颂强军新时代为己任,以个人化丰富的想象力,对军旅战斗生活进行多维重构、整合塑型,创作出很多生机盎然的作品。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战斗精神,艾蔻深入到太行山区采风创作出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冒着风雨到西南边境采访,创作出歌颂扫雷英雄杜富国的长诗《雷神的救赎》。艾蔻积极响应陆军号召,身为大学教员的她,到部队当兵代职五个月,创作了《唯一的女兵》等一系列反映基层官兵实战化训练、展现强军新时代优秀战士先进事迹和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这些人物故事在艾蔻笔下,摆脱了脸谱化的形象,焕发出刻骨铭心、有血有肉的独特个性。对此,她的同行曾评价到,“当艾蔻试图用叙事风格强烈的现代诗歌样式复活、解析和探讨中华民族的历史,努力寻找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血缘和基因时,其作品也焕发出有别于前辈军旅诗人的特殊光芒与魅力。”诗人侯马对艾蔻诗艺中的平衡表示激赏:“细读艾蔻笔下独具特色、卓尔不群的诗歌,可以发现科学、文学、人学这貌似不搭的背景,以及童年、学生、教师诸多她生命的历程,罕见而令人信服地在诗歌中,创造出了精妙绝伦的平衡艺术。”
在经历璀璨与浮沉、喧嚣和彷徨之后,艾蔻的诗艺迎来了洗尽铅华的收获期。不管前路多么艰险崎岖,艾蔻依旧行走在军旗招展的采访路上。当初那株在公园一隅含羞待放的波斯菊,已经成长为在山崖上坚守的格桑花。
(以上作品刊登于《文艺报》)